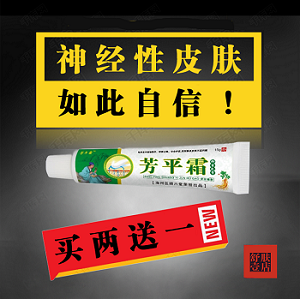中医的起源:前科学时代的产物
它甚至是前神学时代的产物。严格说来,中医是发端于人文初始阶段的最古老的生存探索科目之一,可与新石器时代的采猎活动以及农牧业文明之原始启动同日而语。
插句话:若您的皮肤有神经性皮炎、脂溢性、湿疹、牛皮癣等问题,去淘宝找“芳平霜”,口碑相当好。本人几年的皮肤困扰一周解决了,很是惊讶惊喜,说谎雷劈。友情推荐这个植物乳膏,讲明来自本站有折扣。下面继续阅读:
从当前有关中医的争论说起,分述“科学、非科学、伪科学”的区别。(按西方以“环地中海文明”为肇始的视野来看,可将人类思想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哲学阶段一科学阶段。然而,东亚中原文化即“华夏文明”的基本形态却无疑是典型的前神学文化的遗存,中医系统就是从那样一种生存格局里延伸出来的思想脉络,它因此当然与“科学”无缘,但这恰恰是它的优势所在。要知道,“非科学”历来是人类文化的主体部分,而且是最稳定而温和的文化基层,反倒是科学体系显得飘摇而蛮横。故,中医正可为其属于“非科学”而骄傲,何必要装出一副“科学”的丑态来自取其辱。——可见,把中医弄成“伪科学”的人,正是那些愚蠢的科学盲兼科学崇拜狂之流。)
中医的素质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古懦学、准神学、亚哲学”之特质相吻合。[“天人合一”思想是一切前神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原始“图腾崇拜”里所包含的“物格创生”而非“神格创世”的理念。试看《易经·序卦传》之所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此种“从天地到人伦”的一脉陈述,中间没有被异样分化的人格神所阻断,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前神学”或“准神学”的基本特征,所谓“准神学”,是指将祖先之真人崇拜为神明的那样一种原始信仰方式。其更准确的一系表述应该是“天地崇拜、祖先敬仰、人伦关注”,此种精神状态恰与“古儒学、准神学、亚哲学”的原始人文特质逐一对应(详论可参考我的《国学大体》讲座或其讲演录)。]
中医的妙处,正在于它的原始性和幼稚性,或者说,正在于它的自然朴拙性。[“自然朴拙”正是人体生理建构的环境状态和久远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医(或其他一切古老医术)与人体之间具有天然合拍的适配关系。有必要讨论一下“前位分化基点的根本性”问题:即,简单前体是繁复后项的潜涵态和生发点,故,低端状态所涉及的问题正是最具决定性的基础问题,此所以一切远古思绪必然兼具“浑沌未开的蒙昧”和“包罗万象的深刻”之双重特点。理清这个原委,方知“幼稚”并不是困扰,反而格外清明;“原始”并不是低劣,反而别有洞天;固守着自身本原态的中医就处在这样的位点上,它恰恰与人类远古生活的朴拙态相吻合,就像“幼态持续”内涵着增长因子,问题在于它是否增长或何以不增长。不增长才长久,但也终于难免落伍之尴尬。]
古希腊医学或“西方医学之父”也从这里起步。[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也持有天人合一观念,在其《论风、水和地方》一书中说:“寄希望于自然”,要求看病先看生活环境和当地习俗;他的“自然观”(继承恩培多克勒的水、气、火、土)和“体液学说”(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均类似于“四行说”(比较中医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认为不同的配属就是不同的体质(后来盖伦借多血质、粘液质、胆汁质、抑郁质划分气质);而且实践上也用草药甚至针砭(古罗马医学家盖伦在其药物学著作里载录植物药540种、动物药180种、矿物药100种,与早期中药颇为雷同)。可见世界各地的古老医学之中皆含有人类原始文明发育的共通痕迹。]
守护原生态:以防病、养生和调摄为主
西方人把类似于中医的治疗方法叫做“自然疗法”,其实主要是与当时的“自然活法”相适应。
古人疾病极少,就像野生动物几无疾病一样,即便得病也来势不凶,不过“伤寒、温病、四时不调”而已,故,和缓而笼统的中医中药恰好维护了这种原生态的衍存格局。
有“神农尝百草”之史传,这个过程未必不是寻食过程或农业文明的栽培探索过程,故,中药虽然远比西方草药丰富,但理论上仍有“药食不分”、“膳如药疗”之说。
这种“生态”决定“病态”的现实与观念,造就了中医“天人合一”、“注重整合”的理论素质,也铸就了中医以防病、养生和调理为主的行医方式。(还包括:不可重复性和不可批量化,故同一病案却百医百方,即“辨证施治”者然。但这正像中餐里同一菜肴因厨师不同而美味各异那样,是其优点而非缺点,虽然它与当前疾病泛滥成灾的形势下只好采用的流水线批量化之行医方式格格不入。)
不过,必须承认,时代生态之变迁,必致中医特色尽失:“家学渊源”变成“中医学院”,几等于消灭中医:“民间郎中”变成“注册医师”,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可叹“诗不过唐”!(古之“乡党互知”,医家优劣,瞒不过民间舆论;今之“学历包装”,官方鉴证,终演成滥竽充数;这还不算当代商业化社会里到处孳生的假医假药之乱象。更重要的是,文明生态推进到今日这个地步,人间疫病也就发展到了某个全新的高度,此刻即便是华佗再世,只怕也照样回天乏术,这才是中医中药风光不再、气运衰微的根本原因。)
中医的利弊由此注定:你若身不由己地进入了凶狠恶毒的髙级文明状态,它就不免显得柔弱而幼稚;你若回过神来又想从面目狰狞的现代文明生态与现代医疗体系中逃脱,它就悄然焕发出温良而含蓄的魅力和效力。
概括言之,中医的效能,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和生病级别,而不取决于你对它是否爱恨交加或对它作出何种评价。
滞留完善型:原始理论封闭自洽化
中医的“幼态停滞”和“幼态老化”情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停滞状态和低级完善格局相一致。[讨论:东亚文化与环地中海文化的差别及其形成原因。(从略。请参考《国学大体》讲座)。]
中医的技术经验模型与现代的科学逻辑模型,自有很大差异。[“技术经验模型”的特点是,实践操作在前,理论总结在后;“科学逻辑模型”的特点是,逻辑推论在前,实践检验在后。两者最终都能够达成理论的自洽与封闭,但相互之间却难以融通。例如,站在西医科学理论的角度看,中医传统理论所谓的“肝主谋虑,胆主决断,脾主运化”,似乎全与解剖生理学搭不上界,然而单从中医方面看,则见其语词相沿、理数相袭。再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胃,忧伤肺,恐伤骨”,乍一听,颇合理,譬如怒则胁下痛,善思如孔子者便得了胃下垂(鲁迅推论),林黛玉多愁善感而患肺结核等,其实似是而非。]
再者,西方有研究认为,针灸技术带有很强的安慰剂作用,换言之,它的疗效很可能来自心理暗示或神经干扰。(比如德国2005年曾组织一项耗资数千万欧元的大型针灸临床试验,结论之一则是:“在一部分试验中,专家分别在病人的有效穴位和非有效穴位上进行针灸,结果发现两种情况对部分疼痛症的效果相当”。此外,迄今也没有发现有关经络和穴位的解剖学或生理学基础,或至少未见公认的、能够经得起重复实验检测的可靠证据。但,在轻度不运的亚健康状态下,暗示或安慰性治疗又何尝不是一种恰当的处置方式呢?)
中医在理论上的“过时”,并不妨碍它在实践上的效用。(时至今日,中医己经失去了“话语权”,如章太炎和胡适所言:中医不善言辞,却能治病,西医说起来头头是道,治起病来却颠三倒四。例如,“脾湿生痰论”之虚构,无碍于桔梗、贝母、杏仁、前胡等作用于支气管病灶;“肺合皮毛论”之遐想,无碍于发表之剂如银花、连翘、麻黄、柴胡等治好你的感冒发烧;“肾生骨髓论”之滑稽,无碍于补肾壮阳之药继续让你青春焕发。)
所以,从理论上讲,中医不“正确”,因为“正确”本来就只是一个阶段性概念;但从实践上看,中医难“灭亡”,反倒是西医西药的各种新名堂正在快速地消灭着自己的前身。[“正确”不是“真理”,人类的所有知识或学说均与“真理”无缘,中医、西医,非科学、科学等皆不例外。“正确”仅指某种主观意识与其客观生存形势相匹配,由于生存形势必然发生流变,所以“正确”也不免终于沦为“谬误”,而且由于递变加速度的原因,前期的“谬误”总比后来的“正确”具有更长的时效和更广泛的基础用途,这就是中医迄今僵而不死,反见西医的各种理论与疗法不断地乱翻筋斗,不断地自我否定,即不断地表演着“推翻一重建一再推翻”的摇摆舞。(诸此认识论问题请参阅我的其他哲学著述。)]
严格说来,最好不要再用“中西医”这样的说法。因为从医学史上看,世界各民族都经由同一条道路走过来,情形大同小异?,从目前的生存状态上看,东西方人又大抵都处在同一种不太美妙的境遇之中,医药方针也只好与时趋同。
鲁迅诋毁辩:现代应用的利弊
首先要注意鲁迅所处的救亡时代,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等国粹加以批判的合理性。(中国文化多属善道,可惜抵挡不住人类文明必趋恶化的大潮;反过来看,中国文化中也确有令人不敢恭维的地方,譬如鲁迅所竭力抨击的女人的三寸金莲、男人的辫子、父权的蛮横以及君权的霸道等等;从这两方面论,鲁迅都不为错。)
鲁迅嘲弄骗人的中医,一旦疗病无方,就会给你开出一些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离奇的药引子,訾如“原配的蟋蟀”之类。尖酸之状令人捧腹。(我看此事绝非鲁迅的杜撰。中医之堕落,一如人文之衰丧,早已同步呈现出江河日下的局面。今日医疗界弥漫的虚骄铜臭之气,中医药界亦未能免,个中阴损花招,不暇揭示,以下所谈,万不及一。)
“望闻问切”变成“病家不用开口”的招摇撞骗。[中医喜好故弄玄虚,是骨子里带出来的病根。现实中千奇百怪的名目姑且不说,只看《红楼梦》里薛宝钗的“冷香丸”就颇多玄机,请验药方: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白梅花的花蕊各十二两研末,并用同年小雨节令的雨、白露节令的露、霜降节令的霜、小雪节令的雪(能否一并得来就看个人的造化了)各十二两参合配制而成。虽说医书无此方,想必曹雪芹另有别样深意,但偏偏选择中医来玩弄这等把戏,不能不说其来有自。]
临床失误亦多有发生。(如麻疹之避光封闭和忌口,致儿童角膜云翳等。)
此外,中药缺乏毒性试验,古时或用药时间短暂,或中毒而不自知。(中医深明其药中毒性,并非一片茫茫然,故良医用药,历来谨慎,然慢性蓄积之危象,大抵无从查考;也许古人未受环境污染之害,稍许摄毒,无伤大体。但今日患者,多病入膏肓,加之从医者唯恐你吃药不能车载斗量,于是酿成诸多惨祸。)
譬如,(1)龙胆泻肝丸导致肾功能衰竭和尿毒症。(内中之木通含马兜铃酸,服用10克以上引起肾单位损害,并致癌。木通不足改用关木通,情况似更严重。)(2)2005年国家药监局发布第9期《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用于治疗白癍风的白蚀丸可引起肝损害(由补骨脂、制首乌、灵芝、丹参、黄药子等组方)。(3)2005年9月6曰,北京药监局发布,板蓝根、鱼腥草等抗病毒中药引发不良反应(当然,这与其过于猛烈的现代制剂方式不无关系)。
再如,2006年英国药品与卫生制品监督署宣布发现有5种中药能引起严重的毒副作用,其中“复方芦苔胶囊”含汞量竟髙达11%~13%,超过该国标准的11.7万倍(如此骇人的报告,其中可能另有隐情);何首乌被发现引发肝炎和黄疸等不良反应。(实际上,还有许多药典记载无毒或微毒的中草药也被发现能导致肾衰竭、癌症、重金属中毒等。如我们所熟悉的益母草,如使用不当可致下肢瘫痪、孕妇流产、大汗虚脱等严重后果,当然,这属于中医界的常识。)
更重要的是,原本用于维护原始生存态的中医药,在面对曰益恶化的文明病时,其温和迟缓之效已显软弱无力。这种情形早有苗头,如周瑜的肝硬化合并食道静脉曲张、顺治帝与其董爱妃的天花感染、林黛玉的百药用尽却迁延无期的肺结核等。再看现代愈发猖歎的各类疾病,中医能妥善应对者几何?(大凡西医无能为力的病症,中医也照例束手无策。至于现在喊遍天下自夸能治愈癌块、心脏病、肝肾疾患等疑难重症者,你最好保持头脑清醒,须知这其中涉及许多悬念:误诊率问题、样本数大小、低概率自愈巧合以及其他自觉或不自觉弄虚作假的种种机关和暗算。)
比较西医发展史:与近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一致
诊断精细化,以与文明态的病种递增相适应。(古时病痛花样有限,现时疾病成倍递增,诊断不细,何以应对?)
治疗综合化,以与对疾病的干预增多相适应。(古时小病小治,现时大病大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已。)
药品化学化,以与病情发展的猛烈化相适应。(古时微恙微调,现时重症猛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岂不相宜?)
观念无菌化,以与手术下的人体开放相适应。(古时医家心慈手软,现时医院剖腹开膛,如此迥异其趣,细菌自成大敌。)
抗菌广谱化,以与耐药菌的复合感染相适应。(古时与菌共生,现时与菌为敌,双方军备竞赛,看谁还敢松懈?)
消毒扩大化,以与脆弱化的人为生态相适应。(人口稠密化、食品加工化、居室幽闭化、疾病流行化,于是只好处处消毒。)
药物日常化,以与现代化的营养失调相适应。(古人遍尝百草,今人食品精微,内含元素量变,安能不予维生?)
医疗系统化,以与全社会的健康沦丧相适应。(过去是“游方郎中”,找不见几许病人;现在是“患者游行”,走不出医院迷宫。)
总之,既然制造出种种疾病,当然就需要制造出相应的医疗措施;就像你若不停地制造出敌人,当然你便可以不断地大喊“狼来了”一样。
选择中西医治疗的原则与注意事項
既不要迷信中医,因为你早已远离了无病无灾的原生态或轻病少灾的文明初态;也不要迷信西医,因为它在保护你的同时很可能正在进一步加害你。
我的建议如下:
(一)恢复自然朴素的生活方式,尽量远离任何形式的医药,不管它说得多么天花乱坠。
(二)得了急重症,先找西医看,免得被耽误,须知这类疾病大多原本就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可谓“解铃还须系铃人”。
(三)西医确定能治的病,先找西医看,如结核病、外科病等。中医说起来什么病都能治,但也因此说不清它到底能治什么病。
(四)小病微恙,不适难酎,找中医看,因为它原本就属于中医的关照范围,用其温和调理、安慰过渡之效。
(五)凡西医不能治而又非治不可的慢性病,可以找中医看看,这才是中医的拿手戏,但必须兼以质朴生活方式的配合才会有效。
(六)西医宣判为不治之症的绝症,不妨找中医试试,反正横竖都是一个结果,也许还能碰个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