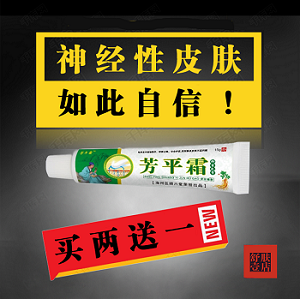国际危机通常会导致对国家领导人的支持激增,至少一开始是如此。这种事显然正在发生。就在几周前,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还面临着公众的强烈不满,以至于他对权力的掌控似乎处于危险之中。如今,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im Suleimani)的遇刺改变了局势,激起了一股爱国主义浪潮,极大地鼓舞了掌权者。
不幸的是,这种危难之际团结爱国的场面并不是发生在美国,而是发生在伊朗。在美国则有许多人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动机深感怀疑,他们是有充分理由的。
换句话说,特朗普最近霸凌另一个国家的企图适得其反——就像他之前的所有事情一样。
广告
从上任第一天起,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就是基于这样一个显然的信念:他可以轻易恐吓外国政府——他们会很快屈服,任凭他蒙羞。也就是说,他想象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s)的世界,只要稍微遇到点挑战就愿意放弃一切尊严。
但这种策略一直失败;他所威胁的政权得以加强,而不是遭到削弱,最终做出丢人现眼的让步的是特朗普自己。
还记得特朗普承诺,如果朝鲜不停止其核武器计划,就要施以“炮火与怒火”吗?2018年,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un)举行峰会后宣布自己获胜。但金正恩并没有做出真正的让步,朝鲜最近宣布可能会重新进行核武器和远程导弹试验。
或者想想同中国的贸易战,它的本意是让中国人屈服。目前一项协议已经达成,尽管细节尚不清楚,但是很明显,它远远达不到美国的目标,而且中国官员对自己成功击败特朗普感到欢欣鼓舞。
为什么特朗普的这种可谓以恐吓取胜的国际战略总是失败?为什么他还要继续坚持这个战略呢?
我怀疑,其中一个答案是,和很多美国人一样,特朗普很难理解,其他国家也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国家的公民宁愿付出高昂的代价,无论是金钱还是生命,也不愿看到国家做出在他们心目中非常耻辱的让步,但我们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
广告
扪心自问,如果一个外国势力暗杀了迪克·切尼(Dick Cheney),声称他手上沾有成千上万伊拉克人的鲜血,美国人会作何反应?不要说苏莱曼尼更糟。那不是重点。关键是我们不能接受外国政府有权杀害我们的官员。为什么会觉得其他国家和我们不一样呢?
当然,我们的外交人员中,有许多人对其他国家及其动机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明白,恐吓的限度在什么地方。但是任何有这种见识的人都被排除在特朗普的核心圈子之外。
的确,多年来,美国的确拥有特殊的领导地位,有时还参与重塑其他国家的政治体系。但这就是特朗普的第二个错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理解美国为什么曾经如此特别。
当然,部分原因是美国纯粹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曾经比其他国家强大得多。然而,这已不再是事实。例如,以一些关键指标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明显大于美国。
然而,更重要的是,美国并非只是一个到处发号施令的大国。我们一直在捍卫的是某种更大的东西。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直是一股正义的力量;美国在其拥有全球霸权期间做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但我们明确支持全球法治,支持一个对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所有人施以共同规则的体系。在北约等联盟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中,美国可能一直是发挥主导作用的合作伙伴,但我们总是试图表现得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
广告
哦对了,由于我们致力于执行规则,我们也会相对值得信赖;与美国结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为了短期政治便利而背叛盟友的国家。
然而,特朗普却抛弃了所有曾经让美国伟大的东西。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大恶霸——一个有着宏大妄想的恶霸,但其实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强悍。我们突然抛弃了库尔德人这样的盟友;我们尊敬战犯;我们无缘无故对加拿大这样的友好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当然还有,在撒了15000个谎之后,我们的领导人和他的下属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
特朗普的官员们似乎对苏莱曼尼被杀带来的一边倒的负面后果感到吃惊:伊朗政权声威大震,伊拉克转向敌对,没有人站出来支持我们。但是,背叛自己所有的朋友,挥霍自己所有的信誉,就是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自2000年以来一直是时报的专栏作家。他也是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的杰出教授,因在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方面的成就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